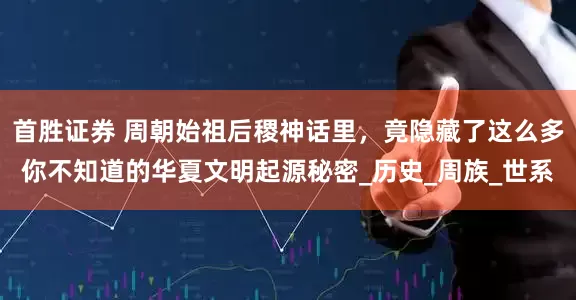鼎冠优配
鼎冠优配
今年是NOWNESS天才计划举办的第7年,舞蹈影像创作实验室也迎来了第三批学员——2023年至今,我们延续与青年演员、舞蹈家尹昉和吴孟珂的合作,邀请到导演饶晓志担任联合导师,开展舞蹈影像创作实验室(Move a Movie Lab)的提案征集,最终收到近百份作品。
我们为什么跳舞?今年的提案大都呈现出更清晰的叙事取向,导师尹昉注意到,不少创作者都在探讨“自我与世界的关系”——从职场到情感,从个体经验到社会背景,舞蹈成为人们理解与表达自我的通道。
尹昉认为,如今舞蹈影像的突破不在于展示非凡的身体技能,而在于如何真正找到身体表达的独特视角——“今年的提案中,不乏有创作者希望尝试素人出演(非专业舞者训练),从日常动作和行为中提取身体语言、打破观众和舞者的无形壁垒;一向以非凡极限身体著称的陶身体剧团,也开始使用素人的身体素材创作《动作世界》,给舞蹈创作带来全新视角。”
最终入选的两份提案,分别是导演曹一诺的《失眠飞行模式》和导演郭容非的《梳头》。前者构建了一个被异化的失语世界,主角选择打破规则约束、重塑自我秩序;后者将视线聚焦在一场舞蹈比赛的后台,女儿在混乱和打结的过程中,追问和抵抗“母亲”这个缺席却又无处不在的概念。
导师尹昉告诉我们,在评选过程中,他会结合创作者的过往作品、注重想法的独特性和可落地性。作为舞蹈影像而言,尤其是在叙事类型中,如何定义和使用身体语言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,“不同舞蹈种类带有不同的地域、文化、社会背景,如何更好地提取舞蹈的属性结合叙事、完成情感表达和视听呈现,创作者的视角很重要”。
而导师饶晓志则更注重当下这份方案的逻辑性——相比套上层层概念的表达,他更欣赏那些从真实出发、用身体探索出的叙事。“创作者为什么要跳舞”、希望通过舞蹈来展现怎样的社会情绪,或是反映自身处境和某种文化议题,是一件更重要的事。
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部作品?导师和导演在面试过程中有哪些碰撞交流?对于即将开始的舞蹈实验,大家又有哪些设想和期待?接下来的时间,我们交给创作者。


《失眠飞行模式》构建了一个被异化的世界,楼宇整齐排列,井然有序。所有人每天都在一样的房间,看着情景喜剧,吃着药片维持生命体征。这个世界观里有自己的阶级,有人被设定为情景喜剧创作者,有人被训练成观众,有人像马戏团动物一样负责表演。
最开始写这个剧本是在2023年秋天。那会我22岁,第一部短片《自由永》很幸运地被观众看到,自己的创作成为了真正的影像——在此之前,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开开心心的小孩,但当人们突然把我当成导演,那种感觉是很微妙的。
在我的世界里,拍电影应该和跳舞一样自由自在、不被拘束,但那段时间,总有人问我什么时候拍下一个片子、最近在搞什么创作,拍电影是有规则的、是要考虑受众的。我有点被束缚手脚,不敢落笔了。

当时我有一种世界在失控、人生不由己的感觉。某个失眠的夜晚,我打开电脑写完《失眠飞行模式》的第一版,很符合我的风格,暗黑暴力。天亮了,这个夜晚的故事被遗忘,静静躺在我电脑里两年——后来的日子里,我学会适应规则写故事,学会观察大家喜欢什么,学会不拍暗黑暴力、拍热血真情,认识很多坚持创作的朋友,但也始终觉得北京的天是灰色的。
直到我搬到了成都、搬家后整理电脑、看到《失眠飞行模式》,回想起那段经历,可能是每个创作者都会经历的成长痛——于是我写了第二版,希望能用更自由、更没规则的方式去创作,也希望创作者能和这些角色一样,打破规则约束,重塑自我秩序。


《自由永》,曹一诺
在《失眠飞行模式》中,主角马维是情景喜剧小丑木偶戏的创作者,厌恶着无意义的创作。马维笔下的演员就像小丑和提线木偶,但另一面,自己也是个被提线的木偶,这种掌控与被掌控的关系贯穿全片,我会用“小丑”与“木偶”的身份不停转换来推进故事。
在声音上,全片的音乐会是一种节奏型搭配音效,比如我会用不同调的“哈哈”、被扭曲异化的笑声,呈现主角身体失控的时刻;声音设计会与舞蹈排练同步进行,我希望这次创作会结合每一次排练舞者舞动的状态,用声音设计为他们搭建一个超现实的空间。

我是第一次拍摄舞蹈短片,也是第一次进行舞蹈相关的创作,我一直很爱玩《舞力全开》(Just Dance),常玩得不知天地为何物,有一种所有细胞都在律动的感觉,自由,这是我对舞蹈的第一印象。
肢体和舞蹈是一种很包容的语言:跳舞的人用他的身体在表达、在叙事,尤其在令人失语的现实环境里,肢体语言便更加动人。所以我认为叙事是最重要的——这部短片里没有一句台词,角色的身体就是他们的嘴,肢体动作就是他们的语言表达,我很期待用身体讲故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。


舞蹈影像《梳头》讲述的是一个女孩在才艺比赛后台,孤独地模仿别的母亲给女儿梳头的动作——渐渐地,女孩的动作陷入挣扎与混乱,幻觉中,“母亲”的身影以粗暴的姿态出现,女孩只能用身体反抗鼎冠优配,最后用梳子刺向那段既渴望又无法承受的情感。
对我来说,“母爱”既是温柔的期待,也可能是一种缺席的伤害。我对母性的想象往往来自别人的描述或是童年的观察,再加上一次次在自己心里反复建构出来的幻想。影片围绕“梳头”这一看似日常却很私密的动作展开,每一次的拉扯、打结和挣扎,都像是在追问和抵抗“母亲”这个缺席却又无处不在的概念。
在这段母女的幻象对决中,我想呈现的也不是单纯的个人记忆,而是一种更普遍的体验:母亲的存在与缺席都可能在女儿心中留下深刻烙印,都可能制造出压抑、对抗,甚至镜像般的纠缠。最终,在混乱和打结中,如何为童年受伤的自己找到一条继续前行的路?这是我想探讨的。


上:《今夜不设防》,郭容非
下:《红姐》,郭容非
在《梳头》中,我会参考法国印象派画家埃德加关于“梳头”的画作,把其中的姿态转化为舞蹈影像的身体语言,这些日常动作会成为舞蹈编排的支点;整体上,我会以现代舞为主,现代舞的自由度和张力不仅能更精准展现女孩的情绪起伏,也与主题呼应——它本身就是对秩序与控制的反抗。
而在这个基础上,我会吸收一些国标舞的元素,这个要感谢导师们在面试时给出的建议!因为国标舞的训练严格、竞争激烈,背后也映照着母亲对孩子的高要求,甚至连发型都不允许出错,这和“梳头”背后的隐喻有着天然的关联,同时,国标舞中一些具有力量感的表达也可以融入编排。
在高潮段落,我希望结合弗拉明戈的脚步和击掌,为场景增加节奏感和张力。我喜欢弗拉明戈里那种痛苦的宣泄和命运轮回的质感,它能成为母女对抗时的能量出口。

我一直很喜欢舞蹈,现代舞、街舞、swing、国标、voguing等都接触过,也都是半吊子。但我挺喜欢这种接触舞蹈的方式,同样的身体部位在不同舞种中被一次次重新塑形,好像我的身体也拥有了多重性格。
遗憾的是我不太有机会成为专业舞者,但成为导演后,我反而觉得可以用影像留住这些舞蹈,让它们以另一种形式和我一起存在——其实拍摄本身也像是一场舞蹈。摄影机的移动、节奏、呼吸,与舞者的身体互动时,就像是另一种“双人舞”。所以在创作里,我希望不仅是记录舞蹈,而是让影像和舞蹈真正共舞。


《额温枪女孩》,郭容非
《梳头》选角需求
少年舞者:
A:8-14岁女孩,擅长国标舞/现代舞
B:8-14岁女孩,国标舞/现代舞 舞感好,同时会演奏琵琶
成年舞者
视觉年龄25-35岁之间,女性舞者,国标舞/现代舞 专业舞者。
有无影视表演经验均可报名
需要全程参加舞蹈排练及影片拍摄。
请将个人介绍、舞蹈视频片段发送至columbustudio@foxmail.com
或添加微信报名:lelecwj


今年投递的舞蹈实验室方案,从年龄结构上讲,创作者都很年轻;从主题上来看,我能从不少方案中看到创作者在现实社会中遇到的工作压力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权力关系,看到他们面对的处境和困惑,也看到某种反抗——再通过舞蹈或者舞蹈影像,不管是完成一种反抗、还是跟自我或对立关系的和解,我觉得都是挺有力量和批判精神的。
在舞蹈影像中,“为什么要跳”这件事对我来讲很重要—— 一言不合就开跳,会让我无法理解它的逻辑性,也会让片子看上去非常晦涩。作为今年舞蹈实验室的导师,比起过往作品,我更关注当下的方案是否体现了这一点。

NOWNESS天才计划舞蹈影像单元展映过一部短片,让我印象很深刻,叫《斐波那契数列》(Fibonacci),它没有那么复杂、把肢体表达做得浮夸,我反而从中找到了一些感受和启发。
有时候看到创作者报过来的一些提案,我会觉得像是在套概念、用肢体去解构,而不是有一个原发的初衷——但跳舞的核心不就是自由表达吗?我想舞动我就舞动,这种舞动的根源并不在于表达一个特别高深的概念,而应该是反过来的,我先去表达,再从表达中慢慢找到探索和延伸。
在我的概念里,舞蹈作为一种表达时,可以是很自由、不受规则限制的;但是当它成为一个作品时,我认为应该有一定的逻辑性。这个逻辑性不是指电影叙事的形态,而是说创作者希望通过跳舞来展现怎样的社会情绪,或是反映自身处境和某种文化议题。在舞蹈影像中,使用身体语言或肢体表达的合理性、逻辑性,我还是希望有一定综合,不要显得那么突兀,这是我在选择方案时会侧重考量的地方。


舞蹈创作实验室过往作品《环岛》,魏德安
从这一点出发,我觉得《失眠飞行模式》和《梳头》两个方案,不论是叙事的逻辑性、跳舞的逻辑性还是肢体表达的逻辑性,我都能看得到她们的自洽,这也是我们最终选择的很大原因。除此之外,她们的故事也更聚集当下、聚焦某个具体家庭中的人物关系,同时也反映出创作者对于这个时代的看法和情绪,这些是让我觉得有趣的地方。
在面试的时候,我一直很关心《失眠飞行模式》究竟会跳什么样的舞蹈,我会觉得它更像一种肢体剧表演,而不一定是某个舞种。后来导演说想尝试默剧,我就觉得很有意思,我认为肢体和节奏的重复可以带来一种荒诞的幽默性以及力量感。《梳头》讲述的故事本身是相对常见的,但结合舞蹈会让我觉得很感兴趣。它本身反映了一种冲突,不管是从父母还是上位者的角度,还是关于驯化和不接受驯化,都很合适用舞蹈、用肢体来表达。在这两个方案中,我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们未来呈现的样子。
我们在看舞台时,看到的往往是全貌、一种大画幅的集体呈现,当然导演也会通过舞台调度让观众聚焦在某些动作上。但当它成为舞蹈影像之后,不论是从视觉的角度、特写、镜头,还是肢体调度的结合,我觉得肯定能实现的是另外一种风味,而这另外一种风味是完全区分于舞台呈现的东西,这也是舞蹈影像、肢体影像能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我觉得它是一个阀门,打开阀门之后,大家必须进入到这种假定性的影像世界里来,这是很有意思的。


舞蹈创作实验室过往作品《未来舞厅》,二高
我觉得在当下,每个青年创作者面对的东西都不太一样。我们做剧团时,也会有更偏作者向和更偏市场向的创作,大家经常会讨论“如何在市场跟作者取向之间做平衡”,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,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。
当我们试图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时候,往往可能会造成一个结果,就是两边都平衡不了。所谓的平衡其实是一种修饰的、粉饰过后的创作态度——这个时代的观众看到“平衡过”的东西,是能敏锐感知到你的意图和创作态度的。我倒是觉得从青年创作者的角度来说,无论是面向市场还是自我表达,只要选好了,就可以往更极致的方向去做,因为其实市场也好,受众也好,都会越来越细分的。
从我的角度出发,我觉得青年创作者未来要面对的挑战可能是,不停地有人会说你要做平衡、说你要兼顾,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是应该找准你的定位、找准你的合伙人,朝着最极致的方向去努力,如何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坚决笃定一些,那才是他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面对的诱惑或者挑战。

2022年起,NOWNESS天才计划邀请青年演员、舞蹈家尹昉与舞蹈家吴孟珂担任联合策展人,与世界知名舞蹈影像节 CINEDANS FEST(荷兰舞蹈影像节)合作,创立了舞蹈影像单元——“身影 Move a Movie”,持续向观众展示着肢体动作、舞蹈艺术作为主体介入影像艺术的可能。



嘉旺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